"音丫头,把这封信给你弟弟送去,他在县城当学徒呢!"孔音娘把一封家书塞进女儿怀里,又往她包袱里塞了两个炊饼,"路上遇见差役老爷就把信给他,千万别自己乱走。"
孔音那年才十六,梳着两根油亮的大辫子,穿着新做的蓝布衫,像只欢快的小雀儿出了村。
谁曾想这一走,就是十年回不了家。
走到半道上下起瓢泼大雨,孔音躲进一座破庙。
等雨停了,山路被冲得七零八落,她转来转去就迷了方向。
"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?"一个满脸堆笑的中年汉子赶着牛车过来,"我正要往县城去,捎你一段?"
可怜孔音不认得,这就是专拐姑娘的人牙子张老三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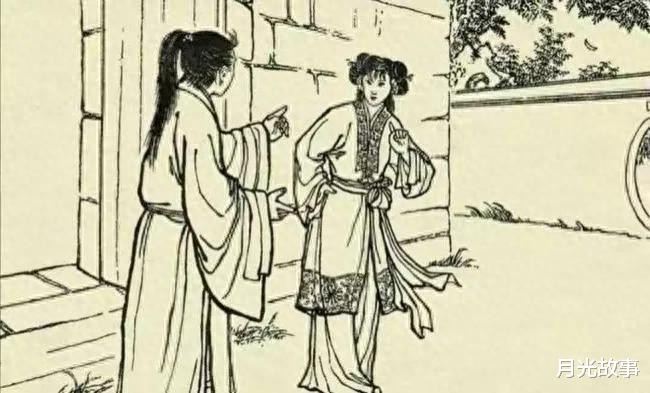
那牛车七拐八拐,越走越偏,等孔音发觉不对时,已经到了一处山坳坳里,四周都是云雾缭绕的大山,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喽!
村里光棍汉们抻着脖子看,聂老汉叼着旱烟蹲在墙根,突然起身往家跑——他家大小子二十三了还没说上媳妇呢!
"闺女啊,这就是你的命。"聂大娘拍着孔音的手说,"咱这地方叫云雾村,十年八年不见个外人。你既然来了,就安心过日子吧。"
孔音捧着粗瓷碗喝粥时,木门"吱呀"一声响。抬头看见个浓眉青年,肩头还沾着柴火屑。
"俺、俺是聂友中。"汉子结结巴巴,手里攥着个编歪的蝈蝈笼。
这聂家大小子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见着姑娘就脸红。
成亲那晚,孔音把娘给的木簪子插在窗缝里,望着月亮直掉眼泪。
聂友中搓着手说:"等开春路好走了,我带你去县城找家书铺,总能打听到你老家。"
后来孔音总想,要是那日没迷路,要是差役按时接到信,要是她没上那人牙子的牛车...
可惜这世上没有"如果"。
这山里的日子啊,就像磨盘似的,转着转着就把人磨服帖了。
孔音渐渐学会了采山货、腌咸菜,就是夜里总梦见家门口那棵歪脖子枣树。
好景不长,成亲才一年,聂友中看见同村的王二从战场寄回银子盖了新房,眼热得不得了。
"媳妇,我去挣军饷,两年就回来!"他扛着包袱走的背影,成了孔音最后的记忆。
三年过去,村里给聂家送来阵亡通知。
村口老榆树系上白布条那天,孔音正给公婆煎药。
公婆抹着眼泪对孔音说:"好孩子,你还年轻,开春有收山货的来,你跟他们走吧..."
"我不走!"孔音"咔"地折断木簪抵住喉咙,"我生是聂家人,死是聂家鬼!"
以死明志的寡妇可不多见,这下可了不得!村里老人都夸她是"贞洁烈妇",族长亲自送来"冰霜节操"的匾,村头孙大娘每回蒸馍都多添两个。
可最近村里人发现,这小寡妇每月初七都往后山破庙跑。庙里就一尊送子观音像,守着个耳背的老尼姑。
"男人都没了,拜什么送子观音?什么贞洁烈妇都是装的,背地里怕是早就和哪个野男人好上了!"王婶子纳着鞋底嘀咕。
这话传到刚回村的聂友时耳朵里,气得他拳头捏得嘎巴响——他是聂友中的孪生弟弟,小时候走丢被货郎收养,头撞石头忘了前尘,如今全想起来了,这才一步步找回家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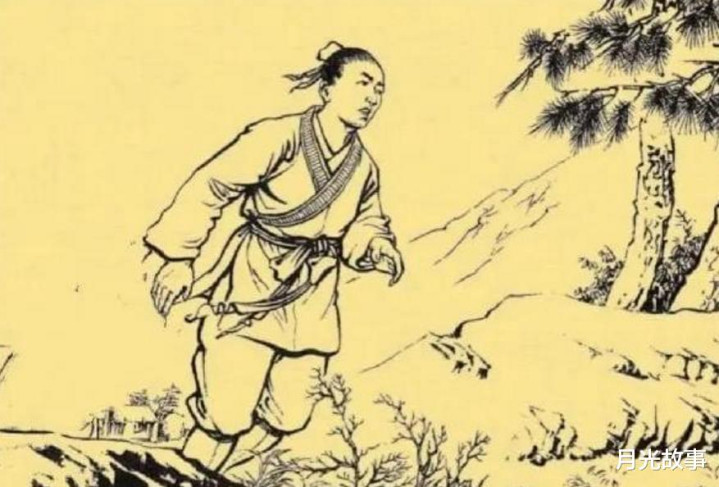
这天初七,聂友时躲在破庙梁上,果然看见寡嫂鬼鬼祟祟进来。只见她从怀里掏出个红肚兜,恭恭敬敬系在观音手上,又往功德箱里塞了张纸条。
"好你个不要脸的!"聂友时跳下来一把抢过纸条,却见上面写着:"求菩萨保佑村东李嫂子怀上娃,信女愿吃素三年。"底下密密麻麻全是村里不孕妇人的名字。
聂友时臊得满脸通红,"扑通"跪下了:"嫂嫂,我...我混账!"
原来他这些年走南闯北,最懂思乡的苦。
第二天他就对全家说:"我要送嫂嫂回老家!"
二老抹着眼泪点头:"是该回去看看。"
只有隔壁张婶子拉着聂友时嘀咕:"如今娶媳妇多难,你娶了寡嫂,既全了兄弟情分,又..."
"婶子!"聂友时打断她,"我嫂嫂为守贞连命都不要,咱不能昧良心!"
出发那日,婆婆把晒好的柿饼塞满包袱:"找着了就捎个信。"
聂友时牵来两头毛驴,驴铃铛上系着红头绳——跟当年货郎拴在他手腕上的一模一样。
这一路走了整整两年。
他们翻过十二座山,遇见过土匪,躲过山洪,终于在第三个年关,找到了那棵歪脖子枣树。树底下坐着个白发老太太,正在纳鞋底呢!
"娘!"孔音一声喊,老太太手里的针线筐"咣当"摔在地上...
后来听说,聂友时在回乡路上碰见了人牙子张老三。
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硬是被打折了一条腿,官府来拿人时,他哭爹喊娘地认了十年前拐卖人口的罪过。
至于孔音?她在娘家住了半年,又带着弟弟回到了云雾村——她说公婆年纪大了,得有人伺候。
这回,村里人经常看见她和聂友时一起上山采药,一个背篓里装着红艳艳的野山枣,一个怀里揣着新雕的木簪子。
